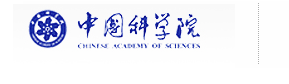母亲的交友史
刘会然
母亲有副热心肠,陌生人和她接触不到三分钟,她就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和人拉起家常。母亲性格又爽直,因此,母亲身边从来不缺少朋友。
老家在江西,改革开放前,母亲也30来岁,在家里干农活。那时,江西地多人少,山上、土里、水里都有丰富的食物资源,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那时,沿海一带还没有开放,很多沿海一带的人由于土地资源相对贫乏,台风等自然灾害严重,浙江、山东、广东沿海一带经常有拖家带口来老家讨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的林场里就有许多广东汉子在耕作。我们村里几口井也是几位山东掘井匠开凿的。很多来自浙江的走街串巷货郎,他们有鸡毛换糖的、有买五金杂货的、也有焗铜补锅,那时老家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外乡谋生者流动的身影。
外乡人来到一个地方,总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我们村是周边最大的一个村落,因此,很多外乡人都会选择来我们村落脚。母亲一看到外乡人来到村里,知道他们颠沛流离的艰辛,很同情他们。母亲每次都很热情的招呼他们来到我家一间没有人住的祖屋,让他们暂时安顿。
在冬天,母亲会帮他们在床板上换上厚厚的稻草。夏天,母亲会帮他们换上新竹席。外乡人一般吃得很粗糙,只要有外乡人安顿在我们家,母亲在炒菜时会故意加些料,并多加一勺油。我们都知道,母亲是想把有余的菜送给外乡人。空暇时母亲总喜欢和外乡人唠家常,假如外乡人有孩子的话,母亲有时还会把我们穿不了的衣服送给他们。
外乡人离开的时候,他们总会客气的说要付点房租。但母亲都是拒绝并爽直地骂他们一顿,说给钱的话,下次就不要来我们村了。弄得外乡人哭笑不得,只好作罢。在我记忆中,母亲那是有很多说得来的朋友,有一群来自山东的胖子叔叔,他们是来村里凿井的;有来自广东的李大伯一家,他们每年春初来放养蜜蜂;还有来自浙江一个姓金的货郎,他的鸡毛换糖现在想起来都甜丝丝的。母亲的这些朋友隔上一两年都会来我家落脚几天,母亲每次都是热情招呼他们,他们俨然成了知心朋友。
改革开放后,沿海一带发展起来了,母亲的那些朋友也渐渐不再出现了。母亲的那些朋友很感恩母亲的厚待,经常会写信告诉母亲他们家乡的巨大变化,他们时不时还会寄上一些东西给母亲,如漂亮的头巾、耐用的塑料制品、实用的小电器等。母亲收到这些东西后都喜滋滋的,她知道那些朋友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再也不用走街串巷谋生了。
新世纪,我大学毕业,在浙江省找了一份工作,也在这里安家了。我把母亲接到了浙江。父母来到浙江后,感叹改革开放后的沿海如此繁荣。
母亲来到我住的小区后,尽管环境有点陌生,但好热闹的她却坐不住,很快她就和小区的那些大妈打成一片。母亲来了这里才发现,一个不大的小区竟然有来自全国东南西北20余个省份的新浙江人。爱好交友的母亲如鱼得水,没有几个月的功夫,就和小区很多年龄相仿的朋友熟悉起来了。母亲来这里之前都是在老家务农,根本就不会外出参加锻炼身体等社区活动。可来到这里后,母亲竟然和一些朋友学起了跳交谊舞、扇子舞等。开始时母亲有点害羞,也跳得别扭,但在朋友的热情教导下,每天傍晚小区的露天跳舞场,总能看到母亲和她那群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在支胳膊扭屁股,一副喜洋洋的神情。母亲说,和她跳舞的有来自东北朝鲜族的老李,还有新疆维吾尔族的哈达木大妈等好多民族的老伯和老太。母亲说,小小的舞台跳动的是一曲多民族的情谊之舞啊。
母亲的一些朋友时常来我家里客厅小坐,我年幼的儿子听到母亲那群天南地北的朋友用带着家乡味的普通话交谈时总是哈哈大笑。母亲也时不时会用电话和那些老朋友联系,经常相邀去参加一些小区的公益活动。有时也应邀去少数民族朋友家里,和他们共同欢庆他们民族的传统节日。
两年前的一天,我在家里看书,门铃响起。一开门,一位中年妇女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你好,你妈妈在吗?”她介绍说她是韩国人,是母亲的朋友。我挺纳闷,说你找错人了吧,我母亲哪里有韩国朋友?那位妇女说,没错,我知道你妈妈的名字。我这才发现,她真的是母亲的朋友。我心里直笑,母亲竟然和异国朋友对接了。母亲回来后才告诉我,那位韩国朋友是几个月前认识的,母亲还得意的告诉我,她的异国朋友不止一个,还有几个来自非洲的黑大伯,美国的琼斯大妈,中东的利比婶等10来位。母亲说这些外国朋友很热情,都会说简易的普通话,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很长见识。
母亲时常邀请她的异国朋友来我家吃中餐。她那些异国朋友也时常邀请母亲去他们家里吃韩国料理、美国西餐或参加生日派对等活动。
前几天,母亲接到了一个来自俄罗斯的越洋电话,原来是她的一位俄罗斯好友回国后给母亲打来的。俄罗斯好友热情地邀请母亲有时间去俄罗斯玩。接完好友的电话后,我发现母亲脸上洋溢着一圈圈幸福的涟漪。
(刘会然,现定居浙江省义乌市,教师,业余作者。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五百余篇在全国百余家刊物发表。著有《陨落的天使》、《父亲的斑马线》等书。本篇为所外来稿。)